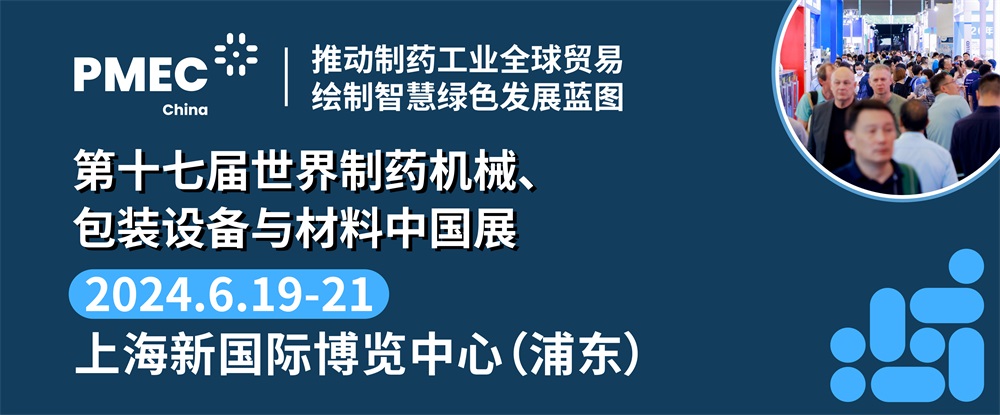作者:方圆
中国医药创新的瓶颈在哪里?
针对这个长期困扰产业界的问题,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答案。美国工程院院士、原力生命科学董事长孙勇奎在首届太湖医药创新大会上指出,中国医药腾飞需要与之匹配的生态实力,现阶段的瓶颈在于以市场为主导的转化医学体系比较欠缺。
反映到产业中是,中国新药研发的内卷非常严重,继上百家公司抢滩PD-1之后,CAR-T也开始遭遇围攻,截至2020年6月,中国CAR-T临床试验数量达到357项,位居全球首位,占比达到53.3%,如今,进入临床阶段的CAR-T疗法多达36款,其中,绝大部分都聚焦在热门靶点CD19。
“创新药的研发需要打开脑洞,寻求突破”,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指出,不同于生物类药容易被模仿、可以快速推进,创新药的研发很难弯道超车,没有探索精神做不出First in Class。
01 雄鹰折翼:中国医药生态的瓶颈在于转化医学?
一般来说,新药的研发流程主要包括,生物学的基础研究、工业界的评估与立项、临床前的研究、早期临床研究、晚期临床研究、工艺生产等六大关键区块。相较于美国市场,中国医药研发的历史比较短,总体来说,中国医药产业在基础研究、项目评估、早期临床研究方面的基础非常薄弱。
“生物医药产业腾飞需要与之匹配的生态实力”,孙勇奎指出,整个生态的所有环节必须齐头并进,倘若某个环节力量特别弱,即便是雄鹰也难以展翅翱翔。作为新药研发的基础,生物学新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但与此同时,针对这些生物学新发现进行项目评估的能力同样至关重要。
“我反对所有人都去做市场”,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、天津大学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何国伟呼吁,整个生态需要有一部分尖端人才去做基础研究,与此同时,还要有一部分人去做转化医学,并且,做转化医学的人需要有临床医学和基础研究两方面的背景,或者推动这两个领域进行合作。
中国过往并未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研究,整个生态的基础研究能力也比较薄弱,加科思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印祥表示,基础研究转化成药物上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过去几十年,医学界有大量的研究并未实现转化,尤其是肿瘤领域,针对现有的研究成果,企业其实完全大有可为。
如今大热的KRA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作为人类定义的第一个肿瘤基因,早在1982年,科学界就从膀胱癌细胞中克隆出了KRAS的致癌基因,却始终没有办法将其开发成药物,一直到2013年,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Kevan Shokat教授找到抑制方法,最终才使这款药物今年刚刚问世。
新药研发需要具备很强的问题解决能力,孙勇奎解释,从立项到临床前的过程中就有很多坑,比如,默克的HIV管线曾面临各种问题,多次差点夭折,从立项到上市,最终花了将近15年时间。
“中国医药创新的瓶颈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转化医学比较欠缺”,在孙勇奎看来,当前的转化医学模式存在很多问题,最常见的就是学术团队为主导、发表文章为目标、转化和产业化效率比较低。
企业主导的市场转化医学体系,最大的特点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,采取市场化的运营,可以根据大学、研究机构、医院等展现出的结果,将针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判断与立项评估节奏往前推。事实上,一旦打通了二者之间的融合壁垒,很多临床上所发现的问题,其实可以用于反哺基础研究。
对此,何国伟认为,中国的医药创新必须着眼于转化医学,从临床上找问题,然后通过自有实验室的基础研究,或者与其他基础研究人员进行合作交流,充分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,然后找到治疗靶点,并通过综合运用器械、药物、疗法、手术等多种手段,最终才能解决疾病困扰。
面向未来,何国伟表示,中国医药生态,除了药物研发,还涵盖了医疗器械、治疗技术、诊疗设备、健康管理等方方面面,仅仅局限于药物创新是不够的,整个生态需要协同发展,共同进化。
02 反内卷?新药研发的制胜关键是产品定位
“中国新药研发正在迎来黄金时代,问题是企业能否抓住时代的机遇。”
针对当前的新药研发局面,沈琳教授将其总结为四个字:多快也乱。比如,从1915年启动血液肿瘤研究开始,中国抗肿瘤的历史其实不过105年,在CAR-T领域,却已经出现了一哄而上的扎堆现象,中国的CAR-T现在基本分布在9个靶点上,主要用于消化道、肝癌和胰腺癌的治疗。
对此,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表示,市场上以抗体为基础的肿瘤免疫治疗,其实还有单抗、双抗和ADC,并且,下一代细胞疗法,CAR-NK的问世也为细胞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。马军指出,CAR-T显然不是唯一办法,但却是有效的办法,所以市场同质化非常严重。
“有些靶点就不要再碰了,太多了”,马军举了一个例子,说明同质化带来的后果,PD-1/PD-L1曾经需要80万一年,现在一年大概3万就够了,经过这次药价谈判,未来可能几千块钱就够了。
“国内的很多创新药企目前仍然是一个开拓者的角色,许多产品都是基于以往十年、二十年的经验在做”,君实生物CEO李宁表示,药企现在需要做的是基于今后十年、二十年的发展趋势,进行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的布局,这就要求企业不仅要发挥自身所长,还需要有充分的市场前瞻性。
“无论对于哪个公司来说,我觉得下一个阶段,对立项的考验会更严峻”,荣昌生物CEO房健民认为,现在产品立项最起码应该是best in class,如果跟着其他人后面做是没有前途的,并且,市面上的项目信披还有时延,通常5年后才能验证项目的真实可行性,一旦砸下去,代价非常大。
面对前有猛虎、后有追兵的市场竞争,房健民认为,下一个阶段,企业需要回到药物研发的本质,从对生物学的基础理解出发,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以及临床的实际需求,找到切入点实现差异化。比如,同样的ADC药物,不同的抗体、不同的毒性小分子、不同的偶联方式,效果截然不同。
“未来最重要的发现,可能会出现在临床研究领域”,房健民指出,“这将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,而不是一拍脑袋就做决定,或者,别人用什么,我也用什么。一款药物往往可能需要做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临床试验,然后从中找到出路,其中,我觉得临床科学家的介入至关重要。”
针对不同的产品定位,研发策略与市场路径也完全不同。比如,生物类似药讲究fast follow,创新药则需要step by step。此外,沈琳教授认为,产品的定位需要立足国际市场,不能只看自己的市场定位,这一点,纳米单抗恩沃利单KN035的整个优化之路,其实提供了许多经验与教训。
事实上,康宁杰瑞的这款产品最早在定位的时候,针对的是一个相对免疫惰性的肿瘤细胞,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相当于进入到了误区,后来沈琳教授的团队发现,这款产品的客观有效率在同类中其实差不多,所以最后在临床I期的时候,重新定位做超人群试验,最终才取得了关键突破。
这种临床实践,不仅给病人带来了更多的生存机遇,也为整个研发生态提供了启示意义。在沈琳教授看来,最有效的研发方式是打通临床团队与转化医学的沟通壁垒,真正做到bench to bed。
03 新药研发很难弯道超车 没有探索精神做不出FIC
不同于生物类似药可以弯道超车,真正的创新药没有捷径可走,两者的研发之路可谓截然不同。
“没有探索精神很难做first in class的探索”,沈琳教授指出,这非常考验临床团队与转化医学团队的实力与心理。毕竟,整个研发过程涉及到转化试验、营养、心理、外科介入、急救、护理等方方面面,并且还需要应对临床试验结果可能不达预期的局面,总体上来说,一定要胆大心细。
“整个过程需要打破框架,寻求突破”,但沈琳教授同时也提醒药企,倘若在研发中确实遭遇瓶颈,该放手是要放手。比如,在C-met抑制剂方面,2015年之前,国内产品一直非常领先,临床效果也很明确,当时没有继续推就在于市场太小,但沈琳教授团队一直在保持跟踪,准备随时重启。
除了临床转化、产品定位与认知框架,在新药研发的过程中,临床试验的质量也尤为关键。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,沈琳教授将影响临床试验的主要因素,总结为六个方面:1.产品的定位;2.产品的性能;3.国内外的研发进展;4.适应症的选择;5.资源的投入与配置;6.市场预见性。
2021年6月,作为国内首个ADC药物,荣昌生物自主研发的玮迪西妥单抗正式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。这款由沈琳教授牵头进临床试验的药物,最初在TDM1研究时,虽然在乳腺癌上成功了,但在胃癌上却失败了,倘若继续做乳腺癌的优效性研究将面临很大风险,如何抉择成了一道难题。
当时,市面上也并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,沈琳教授表示,最终双方来回反复讨论了一年多,这期间临床一期试验已经展开了,并且还是以胃癌为主、乳腺癌为辅,此后,双方决定利用现有的模型与特点另辟蹊径,将胃癌和尿路上皮癌两项适应症作为切入点,并取得了全球领先的临床数据。
“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科学研究的态度,从早期的药物发现、临床前研究,一直到临床研究都需要遵循探索精神”,房健民表示,创新药的研发非常考验企业对科学的理解以及团队的向心力。
除了在ADC之外,沈琳团队在CAR-T上也曾经历类似的考验。比如,针对最具潜力的新兴靶点CACLDN18.2,最早在研发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并进行了更行,但后续进入临床阶段还是遭遇了很多新的难题,并且没有经验可循,最终就是case by case,建立了防治神经毒性的标准SOP。
“我做了几百例缺损修复,没有两个是一样的,深度、高度、位置、大小和传导数的关系都不同”,何国伟表示,他经常会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点,每当下了手术就会把这些病人的血液和DNA分离出来做基因检测,进一步研究这些病人的发病机理,并借此再去设计相应的治疗方案。
具体实践中,针对不同的阶段,提高临床质量的侧重点不同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副主任、院长助力宋玉琴指出,临床前阶段,除了毒理学研究,企业需要临床功课,早期临床阶段,节奏需要张弛有度,尤其在剂量爬坡的时候,晚期临床阶段,需要质量与速度并举,非常考验团队。
“我们经过这么多年下来发现,合作团队是最重要的。首先,研发团队决定了产品的质量,其次,运行团队决定了是否可以随时调整方向,最后,合作团队的能力,决定了是否可以跟上临床步伐,这3个层面,任何一个团队掉链子,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,均会受到很大影响”,沈琳教授表示。



 上一篇
上一篇 下一篇
下一篇